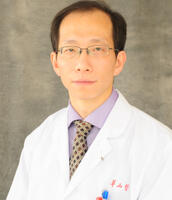焦慮癥其他推薦醫(yī)院 查看全部
焦慮癥科普知識 查看全部
鎮(zhèn)靜和抗焦慮系列問答:問:鎮(zhèn)靜和抗焦慮這兩個概念之間的交集和差異是什么?答:警醒程度由高到低分為過度警醒(焦慮、煩躁)、正常警醒(注意集中聽課)、警醒輕中度下降(思維不敏、有些發(fā)呆----鎮(zhèn)靜)、警醒重度下降(瞌睡----催眠),由此可見,氯硝西泮降低警醒度,當然能抗焦慮。如果降的很精準,達到正常警醒,則不影響學習和工作,這是最理想的;但經(jīng)常沒那么準,會矯枉過正,降至鎮(zhèn)靜水平,對學習和工作多少有一些影響,患者還能忍。如果降到催眠的水平,那就說明降的太過分了,需要氯硝西泮減量。所以,焦慮與鎮(zhèn)靜-催眠是警醒的兩頭,鎮(zhèn)靜-催眠藥降低警醒度,自然就抗焦慮;相反,你要是用阿立哌唑提高警醒度,那就可能加重焦慮。問:剛開始吃氯硝西泮的時候,會有早上起不來床,肌肉松弛等鎮(zhèn)靜效果,可是焦慮卻很明顯答:按理,氯硝西泮上去1小時,鎮(zhèn)靜催眠一出現(xiàn),焦慮就該減輕,你講的“焦慮卻很明顯”難以用藥理解釋。問:吃氯硝西泮兩個月的時候,早上能起來床了,肌力也有了,這是說鎮(zhèn)靜效應逐漸耐受了吧,可是抗焦慮效果卻越來越好答:這是因為藥物打斷了“擔心----增加警醒度-----引起焦慮-----進一步增加警醒度-----進一步加重焦慮”的惡性循環(huán),通過“降低警醒度-----減輕焦慮-----進一步降低警醒度-----進一步減輕焦慮”而回歸良性循環(huán)。問:從我的經(jīng)驗看鎮(zhèn)靜效果會耐受,可抗焦慮效果卻不會答:也會。你忽略了焦慮自身的發(fā)展過程,有的焦慮是開始用藥效果好,過一段時間原來的藥量就不靈了,需要增量,你可以說是藥效耐受,也可以說是焦慮本身在加重;有的焦慮是開始用藥效果好,過一段時間原來的藥量就導致瞌睡,需要減量,這說明焦慮自身在減輕,病人才耐受不住原來的藥量。而你是用藥后,焦慮向良性循環(huán)發(fā)展,逐漸好轉(zhuǎn);鎮(zhèn)靜效應也在耐受,所以療效、副反應都在改善。問:您書里說唑吡坦激動GABA受體上的α1位點,鎮(zhèn)靜催眠,降低警醒度,按理說應該有抗焦慮的效果,但是實際上它只催眠不抗焦慮,這不就矛盾了嗎?答:其實唑吡坦也抗焦慮,但由于唑吡坦的特點是起效快、催眠效力強,持續(xù)作用時間短。具備快、強、短特點的適合用于催眠,不適合抗焦慮,因為抗焦慮希望藥物作用時間長,又不能強到讓病人瞌睡。??問:我看您書里寫的鎮(zhèn)靜和抗焦慮是激動GABAA受體上不同位點導致的?答:有這么回事,那只是不同位點有不同的優(yōu)勢作用而已,相互之間不是絕對孤立的。就像是文科生也學過數(shù)學,只是不如理科生強而已。??問:藥物的鎮(zhèn)靜效能和抗焦慮作用能否劃等號,是否都是降低警醒度?答:鎮(zhèn)靜效能和抗焦慮作用大抵平行,有鎮(zhèn)靜效能的,一定抗焦慮;但反過來說,抗焦慮的未必都鎮(zhèn)靜,例如黛力新、丁螺環(huán)酮、舍曲林都不鎮(zhèn)靜,甚至還有些提高警醒,卻照樣抗焦慮,因為那是走的另一條路,增加5-羥色胺能傳導,以遲鈍情感。馬鞍山市精神病醫(yī)院精神科科普號
為什么治療焦慮癥就得豁得出去?第一,直面核心恐懼,打破惡性循環(huán)焦慮癥的本質(zhì)是對“失控感”或“未知威脅”的過度擔憂,患者常通過回避行為(如避免社交、反復檢查)緩解短期焦慮,卻強化了“危險=回避”的錯誤認知。治療需主動暴露于恐懼情境(如系統(tǒng)脫敏療法),通過反復實踐證明“危險可控”,才能打破回避-焦慮加重的惡性循環(huán)。第二,承受短期痛苦,換取長期自由暴露療法初期可能引發(fā)急性焦慮(如恐慌發(fā)作),但持續(xù)面對恐懼會促使大腦神經(jīng)可塑性改變,降低杏仁核(恐懼中樞)的敏感性。這類似于疫苗接種——通過微量“病毒”激活免疫系統(tǒng),而非完全隔絕風險。第三,重構思維模式,挑戰(zhàn)災難化聯(lián)想焦慮癥患者常將模糊可能性(如“我可能會失敗”)扭曲為必然結果(“我一定會失敗”)。治療需主動驗證災難化聯(lián)想的真實性(如主動嘗試演講并觀察后果),用客觀證據(jù)替代主觀臆斷,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認知沖突與不適。總結:治療焦慮癥的“豁出去”并非魯莽冒險,而是以科學方法主動重塑大腦反應模式,其本質(zhì)是“用可控的短期痛苦,換取長期的心理自由”。廣州醫(yī)科大學附屬腦科醫(yī)院精神科科普號